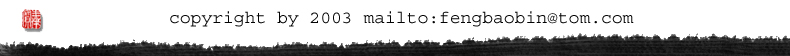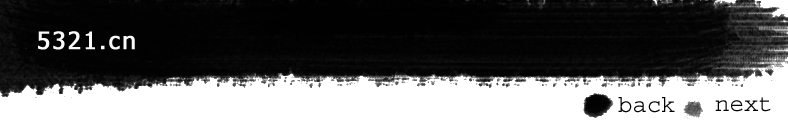
骆宾王的“鹅”
不知是何朝何代,何位高人?在评论某人学识时尽要求背诵一些古诗名句什么的。一些名人的名、字、家境以及他的出生地、每篇文章的出处、原名搬入了纳贤招士的科举应试。流传至今,孩时,就以三岁能背诵一个叫骆宾王写的“鹅”而倍受家人的嘉奖,以至每逢家中有客人或用为他家客人便要牵着那只可怜的“鹅”。钱钟书曾说过:你只管知道鸡蛋不错就行了,何必还要问是那只母鸡下的蛋呢?也有一位叫韩寒的仁兄已将矛头指向了应试教育和当前鼓吹已久的素质教育,有时,我就是想不明白,本是一件好端端的政策和创意。在中国这块古老的沃土上一播种,总能变异成一些不伦不类 的畸形物。我原以为大学教育应该是正统的先进的教育模式罢,且看,凡及文选、汉语之学科无一不是解题,分段,段意,翻译、中心思想,作者背景一套一套的程序地分解,讲解。说白了:所说之处皆为考试之重点也。 语文,文选,汉语之学,目的是让国人掌握祖国的语言工具,熟练地运用好语言文字。而对各种文学典范的学习是领悟千年来各位语言大师的言语技巧和述说方式。目的是学以致用。绝不是让你记下作者字什名谁,有人戏言,古言中的通假字便是大师们的“别”字,虽无从考证,但也不无道理。故外国人说:中国人是学习本国语言最久的国度,但真正对汉语运用自如的人有几?严格,公式的教育方式,多少抹去了国人许多独特开放的思维,完全被世俗的框框囚禁了。 试想:一个能诵诗百首,名句随口而出的人,未必就能有惊世之作,人的精力有限,兴致不同,而且没有社会的实践,生活经历,空有满腹经论也只是空乏之谈,而无实质意义了。有时,理论的东西得遵循事实,厌学之风高涨多年,从以往的读书入仕到今天的知书达理。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进化。社会对读书,考试还是费解之处甚多。教育是科技之本,是衡量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再也不想看到许多学时儿童牵着那只可怜的“鹅”走亲串友。不破不立,教育改革需从根做起,修剪枝叶不伤皮毛,换梁改柱只是做样子给外人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