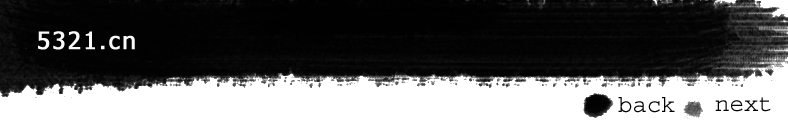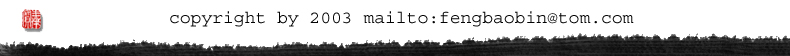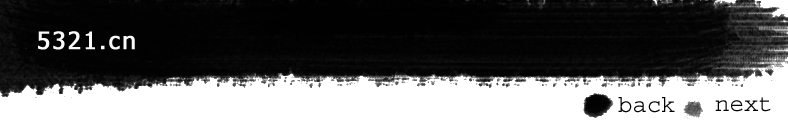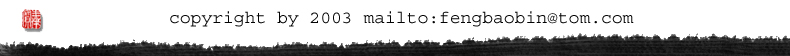梦见童年
常常是在深夜醒来,大约十一点左右,这个时候,室友们轻轻的鼾声,小闹钟滴嗒滴嗒地走着,走廊外的路灯是彻夜不眠的。
敞开的窗户飘荡着月季花香的气息,校园里大丛大丛的花丛像一堵篱笆实实地围着整幢学生宿舍。夏季来临,正值花开时节,微风拂来,簇簇绽放的花瓣像波涛般涌动,一阵阵花香袭向我的眉目鼻息。我闭上眼睛,侧卧着身子,用微红的双颊感觉感受着这阵阵花音的起伏,眼睑微微地颤抖,恍惚地进了一个隔时的时空,一只乌黑的鸦雀扑地飞过窗前窜进密密的林丛里,听着宽大的翅膀拍打声,你会想象到从那温暖的翅腋里掉下来几根细细的绒毛,飘在淡淡的月季花香里,悠悠的。
我穿上白衣黑裤和那双白袜子,拉上门,穿过熟悉的走道,迈着极大的步伐,好像是赶路在返乡的村间路上,路旁夹道的女贞已透着星星点点雪白的小花朵,树下传来窃窃私语,走近看,童年的小伙伴聚在树下摆放着一只苍蝇,诱引着一大群的蚂蚁,此时已聚来一大群蚂蚁,密密地爬在苍蝇周围,稍不注意,还以为是掉在地上一颗黑色的钮扣。孩子们是很仔细的,憋着呼吸,瞪大着眼睛,企图观看着每只小蚂蚁啃下每口食物,待到大头蚂蚁出现了,我们称它是“周扒皮”,大大的脑袋,像高玉宝中的老地主,地面上也只剩下两只翅膀了,几双肥胖的小脚毫不留情地踏在这一群寄生虫上,每人吐上一口唾沫,一窝蜂跑了。
苦楝树下和干墙脚是我们乐园,离三叔公种下的老枫树不远有一间时间久远的老房屋。四周的水砖墙已被炊烟熏得黑乎乎的,斑剥的墙壁上有几颗大大的布满铁锈的钉子,这里曾居住着老四伯一家,后来唯一的女儿嫁到了台湾,前年举家迁过去了,留下这几间土房。屋前的木篱笆早已腐烂泥土了,几根藤箩顺着屋檐爬上房梁又从天窗边延伸到屋里来,一些碎瓦片被雨水冲落下来,长出绿绒的苔藓,翻开瓦片来,常常会遇见蟋蟀,我们就用草枝驱赶它,直到钻进墙缝里去,又时也会是蜈蚣,这时女孩子是会被惊吓的,大叫一声,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窥着地面,男孩子们当然会表示一番男子汉气概了,拾起一块大石块主持正义,那是夏天,穿着露出脚趾的凉鞋,是不敢用脚去踩的。最奇妙的是,一抬头望见在瓦缘边搭网的白蜘蛛了,犹如晶莹细韧的蛛网紧紧地托着一只八条长腿的大白蜘蛛,背上背着一个圆圆的白而透明的“蛛丝包”,凭着日光的照射也能看见鼓鼓的袋囊里一缕一缕缠成一大圈的珠丝,像隔壁五奶奶的满头白发。在高空中“搭房”是很危险的,只见它小心的踏着一根丝上,一颤一颤,慢慢地挪动,突然,从网上滑跌下来,小伙伴“啊”的一声,张大着嘴巴。一个眼尖的发现的秘密:“屁股后有根丝牵着它呢”!“哈哈,真有一根”。就这样仰着头看上一个半小时,大家是不说累的,直到,大白蜘蛛移到了网中央,一动不动了。大伙才依依散去。
常聚在一块的小伙伴也有暂时的分别,一到假期,家里人要携上大包小包去看亲戚,当然这样的事自然要带上小孩了,去亲戚家要先坐一个小时的汽车,再坐木制的汽船走水路二十里,下了船还有七八里的山路。这么远的路程,要很早地起床动身。夕阳斜射到家门口,门前的晒谷场像一面金色的镜子,小伙伴说:明天不能跟你玩了。她的眼睛晶亮,论辈份,她还是我的四姑姑,但是月夜下的迷藏和野战游戏是不分辈份的。妈妈也在为明天去舅娘家打点东西,掐着指头点算着她应该备礼的份数:大小舅娘老外婆三个表哥大小表侄和还没见面刚满月的小表侄孙。桌面是摆满了刚刚出笼的点红的糕点,自家浸制的红枣酒,打发给小表侄孙的红包,桌子下面,两只大灰鹅两双大蹼脚被一根红绳捆的严严实实,一对大翅膀扑扑地拍着地面。出门了要好好打扮一番,妈妈从深红衣柜里拿出刚刚熨烫过的白色套装,放在枕边,以便明天一早醒来就穿上,还一再叮嘱要爱干净,不要到处去野。夜里,我一直缠着妈妈问:那未见面的小老表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胖胖的小脸,小小的鼻子,小小的手掌和脚丫子,还是……
“嘿,嘿,兄弟醒醒,醒醒,八点钟了,该起床了。”
“昨晚什么时候蚊香灭了,被蚊子咬了好几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