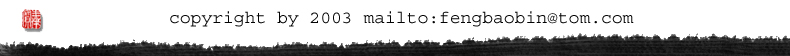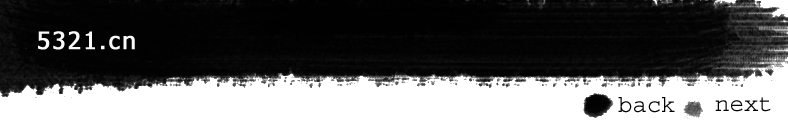
惜字炉与土地庙
听别人讲,离校两里路远的钱家塘有一处土地庙。每日晨跑都有路经,却从未去一探究竟。挑了个有风的下午,踏着浅绿的春草,绕着盘旋在山腰间的渠道,穿插出座落在密林的小山村——狮子尾。这是一个年轻的小村寨,说它年轻是因为它是最近几年从旁边村庄搬迁出来,村寨里被岁月风化的残墙上,还能清晰地辨出文化大革命和学大寨时的口号和标语,淡黄的墙壁上朱红的字迹,向我这述说着当年的情形。 树荫中最多的要数梨树了,正值仲春之季,绽放梨花,开满了山头,一簇簇,一层层,让人不禁想起杨朔的驿路梨花,和冰心笔下日本富士山脚的樱花节。带着沿路的瑕想,呼吸着清新的花香。穿过密密的梨树林,再沿着弯曲的小沟绕到山背后,便到了钱家塘。 土地庙只是当地的一种地方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谁不企求人杰地灵。这或许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文化吧。但思索背后,总感觉这种文化后面含有一种茫目,一种迷信,一种狭隘的追求和崇拜。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惜字炉”时,心里燃起一种莫名的崇敬,或许是因为识得几斗字,念过几日书的缘故吧。目视着青黑的塔身,思索良久,追朔着它的过去,想着数百年前,成群的人们领着自家的小孩手持字条,在炉前焚烧,那样虔诚,那样认真,双手合十,口中虔诚祈祷望着随风飘出的青烟,缠绕而上,飞向青天……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塔,我见到塔内塞了几个易拉罐,还有些零散的碎石。赶集的人们累了,靠着塔身歇会脚,从未谁注意它的存在…… 它原本就在这,百年不移。跟前面的土地庙一样存在。而我认为:不会就这般简单吧,世上没有无缘无固的存在,也没有不明不白的消亡。 |